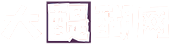陈留阮籍,谯国嵇康,河内山涛,三人年皆相比,康年少亚之。预此契者:沛国刘伶,陈留阮咸,河内向秀,琅邪王戎。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,肆意酣畅,故世谓“竹林七贤。”
阮籍遭母丧,在晋文王坐进酒肉。司隶何曾亦在坐,曰:“明公方以孝治天下,而阮籍以重丧,显于公坐饮酒食肉,宜流之海外,以正风教。”文王曰:“嗣宗毁顿如此,君不能共忧之,何谓?且有疾而饮酒食肉,固丧礼也!”籍饮啖不辍,神色自若。
刘伶病酒,渴甚,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,涕泣谏曰:“君饮太过,非摄生之道,必宜断之!”伶曰:“甚善。我不能自禁,唯当祝鬼神,自誓断之耳!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: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,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,一饮一斛,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。”便引酒进肉,隗然已醉矣。
刘公荣与人饮酒,杂秽非类,人或讥之。答曰:“胜公荣者,不可不与饮;不如公荣者,亦不可不与饮;是公荣辈者,又不可不与饮。”故终日共饮而醉。
步兵校尉缺,厨中有贮酒数百斛,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。
刘伶恒纵酒放达,或脱衣裸形在屋中,人见讥之。伶曰:“我以天地为栋宇,屋室为(巾军)衣,诸君何为入我(巾军)中?”
阮籍嫂尝还家,籍见与别。或讥之。籍曰:“礼岂为我辈设也?”
阮公邻家妇有美色,当垆酤酒。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,阮醉,便眠其妇侧。夫始殊疑之,伺察,终无他意。
阮籍当葬母,蒸一肥豚,饮酒二斗,然后临诀,直言“穷矣”!都得一号,因吐血,废顿良久。
阮仲容、步兵居道南,诸阮居道北。北阮皆富,南阮贫。七月七日,北阮盛晒衣,皆纱罗锦绮。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(巾军)于中庭。人或怪之,答曰:“未能免俗,聊复尔耳!”
阮步兵丧母,裴令公往吊之。阮方醉,散发坐床,箕踞不哭。裴至,下席于地,哭吊喭毕,便去。或问裴:“凡吊,主人哭,客乃为礼。阮既不哭,君何为哭?”裴曰:“阮方外之人,故不崇礼制;我辈俗中人,故以仪轨自居。”时人叹为两得其中。
诸阮皆能饮酒,仲容至宗人闲共集,不复用常杯斟酌,以大瓮盛酒,围坐,相向大酌。时有群猪来饮,直接去上,便共饮之。
阮浑长成,风气韵度似父,亦欲作达。步兵曰:“仲容已预之,卿不得复尔。”
裴成公妇,王戎女。王戎晨往裴许,不通径前。裴从床南下,女从北下,相对作宾主,了无异色。
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。及居母丧,姑当远移,初云当留婢,既发,定将去。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,累骑而返。曰:“人种不可失!”即遥集之母也。
任恺既失权势,不复自检括。或谓和峤曰:“卿何以坐视元裒败而不救?”和曰:“元裒如北夏门,拉(手罗)自欲坏,非一木所能支。”
刘道真少时,常渔草泽,善歌啸,闻者莫不留连。有一老妪,识其非常人,甚乐其歌啸,乃杀豚进之。道真食豚尽,了不谢。妪见不饱,又进一豚,食半余半,迺还之。后为吏部郎,妪儿为小令史,道真超用之。不知所由,问母;母告之。于是赍牛酒诣道真,道真曰:“去!去!无可复用相报。”
阮宣子常步行,以百钱挂杖头,至酒店,便独酣畅。虽当世贵盛,不肯诣也。
山季伦为荆州,时出酣畅。人为之歌曰:“山公时一醉,径造高阳池。日莫倒载归,茗艼无所知。复能乘骏马,倒箸白接篱。举手问葛强,何如并州儿?”高阳池在襄阳。强是其爱将,并州人也。
张季鹰纵任不拘,时人号为江东步兵。或谓之曰:“卿乃可纵适一时,独不为身后名邪?”答曰:“使我有身后名,不如即时一杯酒!”
毕茂世云:“一手持蟹螯,一手持酒杯,拍浮酒池中,便足了一生。”
贺司空入洛赴命,为太孙舍人。经吴阊门,在船中弹琴。张季鹰本不相识,先在金阊亭,闻弦甚清,下船就贺,因共语。便大相知说。问贺:“卿欲何之?”贺曰:“入洛赴命,正尔进路。”张曰:“吾亦有事北京。”因路寄载,便与贺同发。初不告家,家追问迺知。
祖车骑过江时,公私俭薄,无好服玩。王、庾诸公共就祖,忽见裘袍重叠,珍饰盈列,诸公怪问之。祖曰:“昨夜复南塘一出。”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,在事之人,亦容而不问。
鸿胪卿孔群好饮酒。王丞相语云:“卿何为问饮酒?不见酒家覆瓿布,日月糜烂?”群曰:“不尔,不见糟肉,乃更堪久。”群尝书与亲旧:“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,不了麴糱事。”
有人讥周仆射:“与亲友言戏,秽杂无检节。”周曰:“吾若万里长江,何能不千里一曲。”
温太真位未高时,屡与扬州、淮中估客樗蒱,与辄不竞。尝一过,大输物,戏屈,无因得反。与庾亮善,于舫中大唤亮曰:“卿可赎我!”庾即送直,然后得还。经此四。
温公喜慢语,卞令礼法自居。至庾公许,大相剖击。温发口鄙秽,庾公徐曰:“太真终日无鄙言。”
周伯仁风德雅重,深达危乱。过江积年,恒大饮酒。尝经三日不醒,时人谓之“三日仆射”。
卫君长为温公长史,温公甚善之。每率尔提酒脯就卫,箕踞相对弥日。卫往温许,亦尔。
苏峻乱,诸庾逃散。庾冰时为吴郡,单身奔亡,民吏皆去。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,蘧篨覆之。时峻赏募觅冰,属所在搜检甚急。卒舍船市渚,因饮酒醉还,舞棹向船曰:“何处觅庾吴郡?此中便是。”冰大惶怖,然不敢动。监司见船小装狭,谓卒狂醉,都不复疑。自送过浙江,寄山阴魏家,得免。后事平,冰欲报卒,适其所愿。卒曰:“出自厮下,不愿名器。少苦执鞭,恒患不得快饮酒。使其酒足余年毕矣,无所复须。”冰为起大舍,市奴婢,使门内有百斛酒,终其身。时谓此卒非唯有智,且亦达生。
殷洪乔作豫章郡,临去,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。既至石头,悉掷水中,因祝曰:“沈者自沈,浮者自浮,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。”
王长史、谢仁祖同为王公掾。长史云:“谢掾能作异舞。”谢便起舞,神意甚暇。王公熟视,谓客曰:“使人思安丰。”
王、刘共在杭南,酣宴于桓子野家。谢镇西往尚书墓还,葬后三日反哭。诸人欲要之,初遣一信,犹未许,然已停车。重要,便回驾。诸人门外迎之,把臂便下,裁得脱帻箸帽。酣宴半坐,乃觉未脱衰。
桓宣武少家贫,戏大输,债主敦求甚切,思自振之方,莫知所出。陈郡袁耽,俊迈多能。宣武欲求救于耽,耽时居艰,恐致疑,试以告焉。应声便许,略无慊吝。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,与债主戏。耽素有蓺名,债主就局曰:“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?”遂共戏。十万一掷,直上百万数。投马绝叫,傍若无人,探布帽掷对人曰:“汝竟识袁彦道不?”
王光禄云:“酒,正使人人自远。”
刘尹云:“孙承公狂士,每至一处,赏玩累日,或回至半路却返。”
袁彦道有二妹:一适殷渊源,一适谢仁祖。语桓宣武云:“恨不更有一人配卿。”
桓车骑在荆州,张玄为侍中,使至江陵,路经阳岐村,俄见一人,持半小笼生鱼,径来造船云:“有鱼,欲寄作脍。”张乃维舟而纳之。问其姓字,称是刘遗民。张素闻其名,大相忻待。刘既知张衔命,问:“谢安、王文度并佳不?”张甚欲话言,刘了无停意。既进脍,便去,云:“向得此鱼,观君船上当有脍具,是故来耳。”于是便去。张乃追至刘家,为设酒,殊不清旨。张高其人,不得已而饮之。方共对饮,刘便先起,云:“今正伐荻,不宜久废。”张亦无以留之。
王子猷诣郗雍州,雍州在内,见有(翕毛)(登毛),云:“阿乞那得此物?”令左右送还家。郗出见之,王曰:“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。”郗无忤色。
谢安始出西戏,失车牛,便杖策步归。道逢刘尹,语曰:“安石将无伤?”谢乃同载而归。
襄阳罗友有大韵,少时多谓之痴。尝伺人祠,欲乞食,往太蚤,门未开。主人迎神出见,问以非时,何得在此?答曰:“闻卿祠,欲乞一顿食耳。”遂隐门侧。至晓,得食便退,了无怍容。为人有记功,从桓宣武平蜀,按行蜀城阙观宇,内外道陌广狭,植种果竹多少,皆默记之。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,友亦预焉。共道蜀中事,亦有所遗忘,友皆名列,曾无错漏。宣武验以蜀城阙簿,皆如其言。坐者叹服。谢公云:“罗友讵减魏阳元!”后为广州刺史,当之镇,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。答曰:“民已有前期。主人贫,或有酒馔之费,见与甚有旧,请别日奉命。”征西密遣人察之。至日,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,处之怡然,不异胜达。在益州语儿云:“我有五百人食器。”家中大惊。其由来清,而忽有此物,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。
桓子野每闻清歌,辄唤“奈何!”谢公闻之曰:“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。”
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。时袁山松出游,每好令左右作挽歌。时人谓“张屋下陈尸,袁道上行殡”。
罗友作荆州从事,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。友进坐良久,辞出,宣武曰:“卿向欲咨事,何以便去?”答曰:“友闻白羊肉美,一生未曾得吃,故冒求前耳。无事可咨。今已饱,不复须驻。”了无惭色。
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,桓车骑曰:“卿非田横门人,何乃顿尔至致?”
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,便令种竹。或问:“暂住何烦尔?”王啸咏良久,直指竹曰:“何可一日无此君?”
王子猷居山阴,夜大雪,眠觉,开室,命酌酒。四望皎然,因起仿偟,咏左思招隐诗。忽忆戴安道,时戴在剡,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,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,王曰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
王卫军云:“酒正自引人箸胜地。”
王子猷出都,尚在渚下。旧闻桓子野善吹笛,而不相识。遇桓于岸上过,王在船中,客有识之者云:“是桓子野。”王便令人与相闻云:“闻君善吹笛,试为我一奏。”桓时已贵显,素闻王名,即便回下车,踞胡床,为作三调。弄毕,便上车去。客主不交一言。
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,船泊荻渚。王大服散后已小醉,往看桓。桓为设酒,不能冷饮,频语左右:“令温酒来!”桓乃流涕呜咽,王便欲去。桓以手巾掩泪,因谓王曰:“犯我家讳,何预卿事?”王叹曰:“灵宝故自达。”
王孝伯问王大:“阮籍何如司马相如?”王大曰:“阮籍胸中垒块,故须酒浇之。”
王佛大叹言:“三日不饮酒,觉形神不复相亲。”
王孝伯言:“名士不必须奇才。但使常得无事,痛饮酒,熟读离骚,便可称名士。”
王长史登茅山,大恸哭曰:“琅邪王伯舆,终当为情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