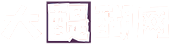豫章太守顾邵,是雍之子。邵在郡卒,雍盛集僚属,自围棋。外启信至,而无儿书,虽神气不变,而心了其故。以爪掐掌,血流沾褥。宾客既散,方叹曰:“已无延陵之高,岂可有丧明之责?”于是豁情散哀,颜色自若。
嵇中散临刑东市,神气不变。索琴弹之,奏广陵散。曲终曰:“袁孝尼尝请学此散,吾靳固不与,广陵散于今绝矣!”太学生三千人上书,请以为师,不许。文王亦寻悔焉。
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。时大雨,霹雳破所倚柱,衣服焦然,神色无变,书亦如故。宾客左右,皆跌荡不得住。
王戎七岁,尝与诸小儿游。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。诸儿竞走取之,唯戎不动。人问之,答曰:“树在道边而多子,此必苦李。”取之,信然。
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,纵百姓观之。王戎七岁,亦往看。虎承闲攀栏而吼,其声震地,观者无不辟易颠仆。戎湛然不动,了无恐色。
王戎为侍中,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,戎虽不受,厚报其书。
裴叔则被收,神气无变,举止自若。求纸笔作书。书成,救者多,乃得免。后位仪同三司。
王夷甫尝属族人事,经时未行,遇于一处饮燕,因语之曰:“近属尊事,那得不行?”族人大怒,便举樏掷其面。夷甫都无言,盥洗毕,牵王丞相臂,与共载去。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:“汝看我眼光,迺出牛背上。”
裴遐在周馥所,馥设主人。遐与人围棋,馥司马行酒。遐正戏,不时为饮。司马恚,因曳遐坠地。遐还坐,举止如常,颜色不变,复戏如故。王夷甫问遐“当时何得颜色不异?”答曰:“直是闇当故耳。”
刘庆孙在太傅府,于时人士,多为所构。唯庾子嵩纵心事外,无迹可闲。后以其性俭家富,说太傅令换千万,冀其有吝,于此可乘。太傅于众坐中问庾,庾时颓然已醉,帻坠几上,以头就穿取,徐答云:“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,随公所取。”于是乃服。后有人向庾道此,庾曰:“可谓以小人之虑,度君子之心。”
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。景声恶欲取之,卒不能回。乃故诣王,肆言极骂,要王答己,欲以分谤。王不为动色,徐曰:“白眼儿遂作。”
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,不与相知。时共集一处,皆当时名士,谓王曰:“裴令令望何足计!”王便卿裴。裴曰:“自可全君雅志。”
有往来者云:庾公有东下意。或谓王公:“可潜稍严,以备不虞。”王公曰:“我与元规虽俱王臣,本怀布衣之好。若其欲来,吾角巾径还乌衣,何所稍严。”
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。公语主簿:“欲与主簿周旋,无为知人几案闲事。”
祖士少好财,阮遥集好屐,并恒自经营,同是一累,而未判其得失。人有诣祖,见料视财物。客至,屏当未尽,余两小簏箸背后,倾身障之,意未能平。或有诣阮,见自吹火蜡屐,因叹曰:“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?”神色闲畅。于是胜负始分。
许侍中、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,尔时已被遇,游宴集聚,略无不同。尝夜至丞相许戏,二人欢极,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。顾至晓回转,不得快孰。许上床便咍台大鼾。丞相顾诸客曰:“此中亦难得眠处。”
庾太尉风仪伟长,不轻举止,时人皆以为假。亮有大儿数岁,雅重之质,便自如此,人知是天性。温太真尝隐幔怛之,此儿神色恬然,乃徐跪曰:“君侯何以为此?”论者谓不减亮。苏峻时遇害。或云:“见阿恭,知元规非假。”
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,名字已显而位微,人未多识。公东出,乘估客船,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。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,当送客过浙江,客出,亭吏驱公移牛屋下。潮水至,沈令起彷徨,问:“牛屋下是何物?”吏云:“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,有尊贵客,权移之。”令有酒色,因遥问“伧父欲食饼不?姓何等?可共语。”褚因举手答曰:“河南褚季野。”远近久承公名,令于是大遽,不敢移公,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。更宰杀为馔,具于公前,鞭挞亭吏,欲以谢惭。公与之酌宴,言色无异,状如不觉。令送公至界。
郗太傅在京口,遣门生与王丞相书,求女婿。丞相语郗信:“君往东厢,任意选之。”门生归,白郗曰:“王家诸郎,亦皆可嘉,闻来觅婿,咸自矜持。唯有一郎,在床上坦腹卧,如不闻。”郗公云:“正此好!”访之,乃是逸少,因嫁女与焉。
过江初,拜官,舆饰供馔。羊曼拜丹阳尹,客来蚤者,并得佳设。日晏渐罄,不复及精,随客早晚,不问贵贱。羊固拜临海,竟日皆美供。虽晚至,亦获盛馔。时论以固之丰华,不如曼之真率。
周仲智饮酒醉,瞋目还面谓伯仁曰:“君才不如弟,而横得重名!”须臾,举蜡烛火掷伯仁。伯仁笑曰:“阿奴火攻,固出下策耳!”
顾和始为杨州从事。月旦当朝,未入顷,停车州门外。周侯诣丞相,历和车边。和觅虱,夷然不动。周既过,反还,指顾心曰:“此中何所有?”顾搏虱如故,徐应曰:“此中最是难测地。”周侯既入,语丞相曰:“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。”
庾太尉与苏峻战,败,率左右十余人,乘小船西奔。乱兵相剥掠,射误中柂工,应弦而倒。举船上咸失色分散,亮不动容,徐曰:“此手那可使箸贼!”众迺安。
庾小征西尝出未还。妇母阮是刘万安妻,与女上安陵城楼上。俄顷翼归,策良马,盛舆卫。阮语女:“闻庾郎能骑,我何由得见?”妇告翼,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,始两转,坠马堕地,意色自若。
宣武与简文、太宰共载,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。卤簿中惊扰,太宰惶怖求下舆。顾看简文,穆然清恬。宣武语人曰:“朝廷闲故复有此贤。”
王劭、王荟共诣宣武,正值收庾希家。荟不自安,逡巡欲去;劭坚坐不动,待收信还,得不定迺出。论者以劭为优。
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,条牒既定,其夜同宿。明晨起,呼谢安、王坦之入,掷疏示之。郗犹在帐内,谢都无言,王直掷还,云:多!宣武取笔欲除,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。谢含笑曰:“郗生可谓入幕宾也。”
谢太傅盘桓东山时,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。风起浪涌,孙、王诸人色并遽,便唱使还。太傅神情方王,吟啸不言。舟人以公貌闲意说,犹去不止。既风转急,浪猛,诸人皆諠动不坐。公徐云:“如此,将无归!”众人即承响而回。于是审其量,足以镇安朝野。
桓公伏甲设馔,广延朝士,因此欲诛谢安、王坦之。王甚遽,问谢曰:“当作何计?”谢神意不变,谓文度曰:“晋阼存亡,在此一行。”相与俱前。王之恐状,转见于色。谢之宽容,愈表于貌。望阶趋席,方作洛生咏,讽“浩浩洪流”。桓惮其旷远,乃趣解兵。王、谢旧齐名,于此始判优劣。
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,日旰未得前,王便欲去。谢曰:“不能为性命忍俄顷?”
支道林还东,时贤并送于征虏亭。蔡子叔前至,坐近林公。谢万石后来,坐小远。蔡暂起,谢移就其处。蔡还,见谢在焉,因合褥举谢掷地,自复坐。谢冠帻倾脱,乃徐起振衣就席,神意甚平,不觉瞋沮。坐定,谓蔡曰:“卿奇人,殆坏我面。”蔡答曰:“我本不为卿面作计。”其后,二人俱不介意。
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,饷米千斛,修书累纸,意寄殷勤。道安答直云:“损米。”愈觉有待之为烦。
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,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,相遇破冈。既当远别,遂停三日共语。太傅欲慰其失官,安南辄引以它端。虽信宿中涂,竟不言及此事。太傅深恨在心未尽,谓同舟曰:“谢奉故是奇士。”
戴公从东出,谢太傅往看之。谢本轻戴,见但与论琴书。戴既无吝色,而谈琴书愈妙。谢悠然知其量。
谢公与人围棋,俄而谢玄淮上信至。看书竟,默然无言,徐向局。客问淮上利害?答曰:“小儿辈大破贼。”意色举止,不异于常。
王子猷、子敬曾俱坐一室,上忽发火。子猷遽走避,不惶取屐;子敬神色恬然,徐唤左右,扶凭而出,不异平常。世以此定二王神宇。
符坚游魂近境,谢太傅谓子敬曰:“可将当轴,了其此处。”
王僧弥、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。僧弥举酒劝谢云:“奉使君一觞。”谢曰:“可尔。”僧弥勃然起,作色曰:“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!何敢诪张!”谢徐抚掌而笑曰:“卫军,僧弥殊不肃省,乃侵陵上国也。”
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,既承藉,有美誉,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。初,见谢失仪,而神色自若。坐上宾客即相贬笑。公曰:“不然,观其情貌,必自不凡。吾当试之。”后因月朝阁下伏,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,左右皆宕仆,而王不动。名价于是大重,咸云“是公辅器也”。
太元末,长星见,孝武心甚恶之。夜,华林园中饮酒,举杯属星云:“长星!劝尔一杯酒。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?”
殷荆州有所识,作赋,是束皙慢戏之流。殷甚以为有才,语王恭:“适见新文,甚可观。”便于手巾函中出之。王读,殷笑之不自胜。王看竟,既不笑,亦不言好恶,但以如意帖之而已。殷怅然自失。
羊绥第二子孚,少有俊才,与谢益寿相好,尝蚤往谢许,未食。俄而王齐、王睹来。既先不相识,王向席有不说色,欲使羊去。羊了不眄,唯脚委几上,咏瞩自若。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,还与羊谈赏,王方悟其奇,乃合共语。须臾食下,二王都不得餐,唯属羊不暇。羊不大应对之,而盛进食,食毕便退。遂苦相留,羊义不住,直云:“向者不得从命,中国尚虚。”二王是孝伯两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