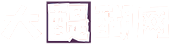《程材》所论,论材能行操,未言学知之殊奇也。夫儒生之所以过文吏者,学问日多,简练其性,雕琢其材也。故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,尽才成德也。材尽德成,其比於文吏,亦雕琢者,程量多矣。贫人与富人,俱赍钱百,并为赙礼死哀之家。知之者,知贫人劣能共百,以为富人饶羡有奇余也;不知之者,见钱俱百,以为财货贫富皆若一也。文吏、儒生有似於此。皆为掾吏,并典一曹,将知之者,知文吏、儒生笔同,而儒生胸中之藏,尚多奇余;不知之者,以为皆吏,深浅多少同一量,失实甚矣。地性生草,山性生木。如地种葵韭,山树枣栗,名曰美园茂林,不复与一恆地庸山比矣。文吏、儒生,有似於此,俱有材能,并用笔墨,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。先王之道,非徒葵韭枣栗之谓也。恆女之手,纺绩织经;如或奇能,织锦刺绣,名曰卓殊,不复与恆女科矣。夫儒生与文吏程材,而儒生侈有经传之学,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。
贫人好滥,而富人守节者,贫人不足而富人饶侈。儒生不为非,而文吏好为奸者,文吏少道德,而儒生多仁义也。贫人富人,并为宾客,受赐於主人,富人不惭而贫人常愧者,富人有以效,贫人无以复也。儒生、文吏,俱以长吏为主人者也。儒生受长吏之禄,报长吏以道;文吏空胸无仁义之学,居往食禄,终无以效,所谓尸位素餐者也。素者,空也;空虚无德,餐人之禄,故曰素餐。无道艺之业,不晓政治,默坐朝庭,不能言事,与尸无异,故曰尸位。然则文吏所谓尸位素餐者也。居右食嘉,见将倾邪,岂能举记陈言得失乎?一则不能见是非,二则畏罚不敢直言。《礼》曰:“情欲巧。”其能力言者,文丑不好,有骨无肉,脂腴不足,犯干将相指,遂取间郤。为地战者不能立功名,贪爵禄者不能谏於上。文吏贪爵禄,一日居位,辄欲图利,以当资用,侵渔徇身,不为将官显义。虽见太山之恶,安肯扬举毛发之言?事理如此,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?儒生学大义,以道事将,不可则止,有大臣之志,以经勉为公正之操,敢言者也,位又疏远。远而近谏,《礼》谓之谄,此则郡县之府庭所以常廓无人者也。
或曰:“文吏笔扎之能,而治定簿书,考理烦事,虽无道学,筋力材能尽於朝庭,此亦报上之效验也。”曰:此有似於贫人负官重责,贫无以偿,则身为官作,责乃毕竟。夫官之作,非屋庑则墙壁也。屋庑则用斧斤,墙壁则用筑锸。荷斤斧,把筑锸,与彼握刀持笔何以殊?苟谓治文书者报上之效验,此则治屋庑墙壁之人,亦报上也。俱为官作,刀笔斧斤筑锸钧也。抱布贸丝,交易有亡,各得所愿。儒生抱道贸禄,文吏无所抱,何用贸易?农商殊业,所畜之货,货不可同,计其精粗,量其多少,其出溢者名曰富人,富人在世,乡里愿之。夫先王之道,非徒农商之货也,其为长吏立功致化,非徒富多出溢之荣也。且儒生之业,岂徒出溢哉?其身简练,知虑光明,见是非审,审尤奇也。
蒸所与众山之材干同也,〔伐〕以为蒸,熏以火,烟热究浃,光色泽润,爇之於堂,其耀浩广,火灶之效加也。绣之未刺,锦之未织,恆丝庸帛,何以异哉?加五采之巧,施针缕之饰,文章炫耀,黼黻华虫,山龙日月。学士有文章,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。本质不能相过,学业积聚,超逾多矣。物实无中核者谓之郁,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。文吏不学,世之教无核也,郁朴之人,孰与程哉?骨曰切,象曰瑳,玉曰琢,石曰磨,切琢磨,乃成宝器。人之学问知能成就,犹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。虽欲勿用,贤君其舍诸?孙武、阖庐,世之善用兵者也,知或学其法者,战必胜。不晓什伯之阵,不知击刺之术者,强使之军,军覆师败,无其法也。谷之始熟曰粟。舂之於臼,簸其粃糠;蒸之於甑,爨之以火,成熟为饭,乃甘可食。可食而食之,味生肌腴成也。粟未为米,米未成饭,气腥未熟,食之伤人。夫人之不学,犹谷未成粟,米未为饭也。知心乱少,犹食腥谷,气伤人也。学士简练於学,成熟於师,身之有益,犹谷成饭,食之生肌腴也。铜锡未采,在众石之间,工师凿掘,炉橐铸铄乃成器。未更炉橐,名曰积石,积石与彼路畔之瓦、山间之砾,一实也。故夫谷未舂蒸曰粟,铜未铸铄曰积石,人未学问曰矇。矇者,竹木之类也。夫竹生於山,木长於林,未知所入。截竹为筒,破以为牒,加笔墨之迹,乃成文字,大者为经,小者为传记。断木为椠,之为板,力加刮削,乃成奏牍。夫竹木,粗苴之物也,雕琢刻削,乃成为器用。况人含天地之性,最为贵者乎!
不入师门,无经传之教,以郁朴之实,不晓礼义,立之朝庭,植笮树表之类也,其何益哉?山野草茂,钩镰斩刈,乃成道路也。士未入道门,邪恶未除,犹山野草木未斩刈,不成路也。染练布帛,名之曰采,贵吉之服也。无染练之治,名縠粗,縠粗不吉,丧人服之。人无道学,仕宦朝庭,其不能招致也,犹丧人服粗,不能招吉也。能削柱梁,谓之木匠。能穿凿穴坎,谓之士匠;能雕琢文书,谓之史匠。夫文吏之学,学治文书也,当与木土之匠同科,安得程於儒生哉?御史之遇文书,不失分铢;有司之陈笾豆,不误行伍。其巧习者,亦先学之,人不贵者也,小贱之能,非尊大之职也。无经艺之本,有笔墨之末,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,虽曰吾多学问,御史之知、有司之惠也。饭黍梁者餍,餐糟糠者饱,虽俱曰食,为腴不同。儒生文吏,学俱称习,其於朝庭,有益不钧。郑子皮使尹何为政,子产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,孔子曰:“贼夫人之子。” 皆以未学,不见大道也。医无方术,云:“吾能治病。”问之曰:“何用治病?” 曰:“用心意。”病者必不信也。吏无经学,曰:“吾能治民。”问之曰:“何用治民?”曰:“以材能。”是医无方术,以心意治病也,百姓安肯信向,而人君任用使之乎?手中无钱,之市使货主问曰“钱何在”,对曰:“无钱”,货主必不与也。夫胸中不学,犹手中无钱也。欲人君任使之,百姓信向之,奈何也?